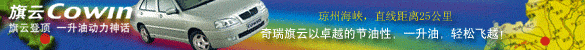对价:承诺后不可反悔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8月30日 09:30 新京报 | |||||||||
|
2005年8月8日的《财经》杂志发表了法学博士高志凯先生的《以“对价之名剥夺财产”》一文(下称“对价一文”),其中的观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觉得有商榷的必要。 财产是可以被剥夺的 对价一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股改中的对价,就是剥夺财产,而剥夺财产大逆不道。
既然财产是可以剥夺的,那就要看剥夺是否经过了正当程序。如果是在美国,如此重大的问题,如果双方相持不下,势必要诉讼,而且是层层上诉,一直告到美国最高法院,最后由9位大法官出面摆平。 在我们这里,如果对价真是剥夺大股东的财产,为何很少见到大股东到法院去诉讼?夫妻离婚分财产,兄弟分家摆不平,都要到法院请法官评断,而大股东损失财产居然能够隐忍不发?大股东不到法院诉讼,可能有几种原因。第一,大股东并没有觉得对价剥夺了其财产。第二,大股东觉得自己的财产虽被剥夺,但并无不公之处———或是说剥夺财产经过了正当程序。第三,被剥夺了,也感到不公平,但无可奈何,觉得到法院告也没有用,于事无补,徒乱人意。或许,大股东可以借用非诉讼手段达到目的。如果大股东真以非诉讼的手段将事情摆平,那也是件很可怕的事。非诉讼手段比较隐蔽,公平、公开、公正从何谈起? 承诺后不可反悔 再看对价。对价是美国合同法中的概念,指履行义务是一种通过讨价还价后达成的交换或承诺。对价的要素是双方有讨价还价的过程,而且有交换。中国常用的名词是“等价交换”。与此相关的概念是“承诺后不可反悔”(promissoryestoppel),即如果承诺造成对方的依赖,则对价成立,承诺方不可悔改。美国《第二次法律重述》第90节第(1)款规定,以下情况出现时就存在依赖: 如果承诺人有理由期待承诺会导致受诺人或第三方有某种作为或放弃某种作为,而且确已诱导受诺人或第三方有此类作为或放弃了作为,如果只有履行该承诺才能避免不公平,则此承诺有约束力。如果出现违约,救济可仅限于实现公平的需要。上市公司当初首公开发行股票时,按照有关规定国有股暂不上市。可以说,当时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减少流通股数量,提高股价,有利于股票的发行。这就是一种诺言,换取更多的投资者购买股票。现在既然非流通股要流通,那就打破了以前的承诺,是一种违约行为,应当有救济。这种救济就是给流通股持有者一些小恩小惠,给他们一些小小的甜头。 不过上述论证也有问题,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规定国有股暂不上市的政府,并不是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第二,当初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购买公司股票的投资者中,今天仍然持有这些股票的已经不多,可以说物是人非,并不是承诺的受诺者。 受让人理应继承并享有转让人的权益 但努力一下,这两个问题也能说得通。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规定国有股暂不上市的是政府不错,但国有股的持有者是国家,与政府是一家,不存在两家人的问题。因此,关于非流通的承诺方可以与国有股股东之间划等号。至于股票易手,尽管流通股投资者已非原始投资者,但并不影响现有投资者享受原有投资者的权益。这就像债权、产权的转让。除非另有规定,受让人理应继承并享有转让人的权益。 当然,利益的不同也导致了视角的不同。所以程序便突显重要了。主流国家通常是通过立法和司法这两个过程来化解问题。首先,由全国立法机构通过法律,以形成共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统一思想。再以议会为大的国家,不仅行业调整等全国性的大动作需要立法机构放行,有时单个企业的改制,也会惊动全国立法机构。 即便立法以人民的名义通过了全国性法律,仍然会有人跳出来反对和阻挠一项革命行动。如果是在美国,少数人———哪怕是一个人———也可以到法院去诉讼,让全世界都听到他的声音。美国是这样,香港也是这样。例如,领汇案中,一位67岁老太太,就通过诉讼阻止香港政府的资产上市,时间长达18个月之久。 美国股市丰富多彩,有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戏法。但这些戏法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与美国的司法和法治有密切关系。比如,美国的券商猖狂无比,但美国股民可以通过诉讼追回损失。美国还有陪审团,陪审团可以裁定被告必须支付高于实际损失数倍的惩罚赔偿。那么比财产法更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以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否可以引进美国一样的股市,并推出胜似美国的股市?这是一个更为困难的命题。 朱伟一(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兼职教授) = 《新京报》服务热线:010-63190000 、010-96096333 = |
| 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财经 > 正文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企 业 服 务 |
| 股票:今日黑马 |
| 投资3万元年利100万! |
| 油价狂涨!钱狂赚! |
| 高血压治疗上的飞跃! |
| 揭开牛仔淘金的秘密! |
| 名品折扣店聚财新模式 |
| 2-5万元投资好项目 |
| 眼镜影院,石破天惊! |
| 美国休闲氧吧,狂赚钱 |
| 看盛唐茶庄如何赚钱? |
| 中国特色治疗精神病! |
| 经营爱情,赚浪漫钱! |
| 拯救男人,还你健康! |
| 男人,更幸福的奥秘! |
| 新韩国快餐一月赚八万 |
|
|
|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