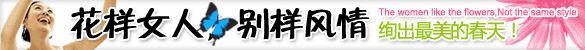|
|
赫伯特·A·西蒙:理论无边界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01日 14:23 《当代经理人》
“我诚然是一个科学家,但是许多学科的科学家。我曾经在许多科学迷宫中探索,这些迷宫并未连成一体。我的抱负未能扩大到如此程度,使我的一生有连贯性。我扮演了许多不同角色,角色之间有时难免互相借用。但我对我所扮演的每一种角色都是尽了力的,从而是有信誉的,这也就足够了。” ——1991年,西蒙在自传《我的生活模型》一书中如此自描 赫伯特·A·西蒙:无学科的科学家 尽管西蒙后期主要从事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研究,但他的学术经历、他的研究方法、他的思想范围,远远不限于单一的心理学。在他那里,科学的分门别类不构成通行的障碍,反而是他前进的标志。他几乎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甚至还有部分人文科学都融汇到了一起。在当代科学发展史上,西蒙是为数不多的那种不需要以学科来限定头衔的大科学家 以管理学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至今只有一人,这就是决策理论大师赫伯特·A·西蒙。同别的管理学大师相比,他看起来貌不惊人、平平淡淡、一团和气、笑容可掬,是那种典型的书院式学者,他身上没有什么别具一格的传说,也没有能引起轰动效应的绯闻或趣事,只是把等身的著作留给了世界。也许,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就是他对国际象棋的痴迷。他似乎要透过那黑白相间的棋盘,参透人类的奥秘。他的理论,对管理学的发展有着方向性的影响。 从管理学家到科学家 西蒙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德国移民,犹太人,电气工程师,受过严谨的德国式大学教育,一生有几十项发明专利;母亲来自一个钢琴世家,在音乐专科学校任教。父亲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对西蒙的性格有着重大影响,而母亲则给他留下了一手出色的钢琴技艺。对西蒙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舅舅哈洛德·迈可尔,迈可尔师从于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在国家工业委员会工作,是他最早把西蒙引上了社会科学的探索道路。 西蒙的天资是过人的,他6岁上学,不足17岁就高中毕业。因此,在高中和大学,他要比同班的学生小两三岁。在同学们中间,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他的聪明、色盲和左撇子习惯。 大学毕业前夕,西蒙结识了里德利,里德利是国际城市管理者协会主任,芝加哥大学兼职教授。西蒙在选修里德利的市政管理课程时,参加了里德利的课题,进行市政管理的计量研究,开始在《公共管理》杂志发表文章,22岁时就成为《公共管理》月刊和《地方年鉴》的助理编辑。西蒙给里德利当助手做出的成就,引起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注意,邀请他设计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地方政府研究项目。1939年,西蒙被伯克利聘为地方政府研究项目的主管。就在这一阶段,他形成了自己对管理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思想,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的主题。这一博士论文,就是他后来赖以问鼎诺贝尔奖的大作《管理行为》的雏形。这时,西蒙已经在事实上进入了管理学家行列。 在朋友的推荐下,伊 利诺伊理工学院聘请西蒙任教。在伊 利诺伊,他深入展开了自己的研究。从他开设的课程来看,他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多面手。他讲授宪法学、城市规划、地缘政治学、合同法、统计学、劳动经济学、运筹学、美国史等等,还开设了科学哲学讨论班,并加入芝加哥大学的考尔斯委员会每周一次的经济学讨论班。伊 利诺伊的经历,使西蒙的管理学研究更为深入,尤其在公共管理领域形成了相应的研究特色,有了如史密斯伯格、汤普森等研究伙伴,同时开始了他以数理逻辑方法融合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起点。 1949年,西蒙应聘到位于匹兹堡的卡内基大学,担任行政学教授和工业管理系主任。在这里,西蒙深入展开组织行为的研究,重视逻辑和理论的教学特点,使卡内基大学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名声鹊起,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哈佛商学院案例教学式的管理教育道路,西蒙的管理学研究,在这里达到了顶点。 1955年,西蒙的研究方向发生了重大转移。在这之前,他虽然在多个学科领域跋涉,但基本上还是在管理学、经济学的大范围内游弋。但这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迟迟早早会导致学术性溢出。在卡内基,这种溢出的火候到了。他在管理学和经济学上的造诣,使他在接触到计算机后,一眼就看出了这种机器有可能带来的奇迹。于是,他立即转向了人类问题解决的心理学研究上,特别是转到对人类用于思维过程的符号处理研究上。从此,西蒙开始了他在计算机技术领域的创新,并赢得了人工智能创始人之一的地位。 尽管西蒙后期主要从事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研究,但他的学术经历、他的研究方法、他的思想范围,远远不限于单一的心理学。在他那里,科学的分门别类不构成通行的障碍,反而是他前进的标志。他几乎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甚至还有部分人文科学都融汇到了一起。在当代科学发展史上,西蒙是为数不多的那种不需要以学科来限定头衔的大科学家。 西蒙后来的研究重点已经不在管理学领域,不过,他对组织与管理的研究成果却使管理学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他提出的决策理论在当代管理学中至今引领着研究潮流。由于他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在1978年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代企业经济学和管理研究越来越重视他的思想,组织行为研究和决策理论已经被成功地用于解释和预测各方面的活动。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言,西蒙是以管理学家身份获得这一殊荣的惟一人士。仅此而论,西蒙虽不敢说是后无来者,但肯定是前无古人。在管理学领域,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组织行为研究、决策程序研究、决策心理机制分析,都具有理论上的开创意义。管理学研究,在这里达到了顶点。 西蒙与国际象棋 西蒙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主要的业余爱好是徒步旅行、钢琴、象棋、绘画及学外语。他对国际象棋情有独钟,痴迷了一辈子。他似乎是要透过黑白相间的棋盘,来参透人类的玄机。在西蒙的眼中,国际象棋几乎就等于人类世界的缩影。从象棋里面不仅可以发现人类的思维习惯,更能解读符号语言的奥妙,从而可以通过计算机来模拟人类的行为。 西蒙从高中时就对国际象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经花了两年时间认真下国际象棋。在高中毕业时,他的棋艺已经相当不错了。那时,城市的娱乐场所在晚上为下棋者大开方便之门,在那里,西蒙遇到了设计出通用下棋评估系统的阿帕德·埃洛,这套系统能够判断出一个棋手处于什么水平--是大师,还是专家,或者仅仅是一个普通的A级棋手。而西蒙则未能突破A级水平。一天晚上,西蒙和埃洛下棋,同往常一样西蒙输了,可他并不甘心。回家后,西蒙重新分析棋局,通过一步步推理,他发现在走第17步棋时如果用象进行正确进攻的话,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对手。 西蒙21岁时,有一次由芝加哥飞往纽约参加专业会议,中途经过底特律、布法罗,并让他第一次从空中看到了美丽的尼加拉多大瀑布。据他回忆,这次旅行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无关紧要的冒险。在曼哈顿,一位贫穷的演员骗取了西蒙的信任,西蒙给他5美元以支付逾期旅馆的账单。在百老汇,他整夜未眠,与失业的象棋大师下棋,每输一盘付25美分。通过切磋技艺,西蒙的棋艺大有长进。西蒙曾一心想达到象棋专家水平,可学术研究与琢磨棋艺不可兼得,只好一直当棋界票友。 1958年,机会来了,西蒙开始研究纽厄尔-肖-西蒙(NSS)国际象棋程序,棋艺同他的学术研究融为一体。于是,他开始经常在匹兹堡象棋俱乐部下棋,很快,他就成了一名老辣的棋手,在城市锦标赛中获得了1853分,水平提高得相当快,甚至击败了当时匹兹堡市最强的对手。但是,棋艺归棋艺,学术归学术,尽管西蒙有着强烈的获胜欲望和不服输心理,但他无法像职业棋手那样把时间全部耗上。即使业余参与,要想保持比赛名次,就必须每星期至少用一两天来比赛。西蒙只好忍痛割爱,放弃了对棋艺的角逐,仅仅保留了一个业余爱好者的本色。象棋终究未能成为他的伴侣,只好永远做他的情人。 假设有人要给西蒙塑像,别忘了,没有国际象棋作陪衬,就难以体现他的风采。 西蒙与中国 管理学大师西蒙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先后来中国访问交流达10次之多。除了他的母国以外,西蒙在中国呆过的时间是最长的。他同中国的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有着多方面的学术合作。学界对西蒙有着业余外交家之称,而这位业余外交家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 西蒙首次来华是在1972年。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坚冰后,中国开始与美国进行科技沟通。于是,美国的计算机科学家代表团来到中国,西蒙在计算机技术上的造诣以及为美国政府服务的成就,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可以说,西蒙以他学者式的洞察力,在这次短暂的访问中就对中国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到1980年他参加美国心理学代表团再次访问中国时,他给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就是按照中国的规矩排列代表团的出场顺序,以适应中国人的习惯和面子。这次访问,使西蒙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达成了学术合作协议,西蒙也根据自己姓名的谐音,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司马贺。短暂的学术交流,使这位司马先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南京师范大学不怎么样的报告大厅,他领教了中国教师努力掌握认知心理学和计算机模拟技术的热诚。从此,这位司马先生开始了自己在中国的学术活动。 此后,他又先后8次来华访问。1983年春,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西蒙教授到中科院心理所进行关于人类短期记忆的合作研究,同时在北京大学系统地讲授了认知心理学。西蒙的夫人多萝西娅则给心理所的人员辅导英语。在历时三个月的系统讲演中,西蒙从理论上讲述了认知科学的基本观点, 阐述了科学理论的层次和规律,分析了物理符号系统和行为选择的满意原则等问题, 还介绍了EPAM程序、启发式搜索等计算机技术的实际应用问题。这次讲课内容后来整理成书正式出版,即《人类的认知--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荆其诚、张厚粲译,科学出版社,1986)。从1984年到1987年,西蒙每年都要来中国工作3周,与中国学术界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他在计算机翻译古汉语、汉字的短时记忆、问题解决和样例学习等问题上,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还亲自指导过中国研究生。 西蒙一向致力于中美学术交流的工作。自1980年起,他一直是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成员,并于1983年至1987年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1985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名誉研究员。此外,他还是北京大学、天津大学、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院等单位的名誉教授。1995年,西蒙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西蒙在与中国同行交往的二十多年中,结识了许多朋友,他的为人处事和治学态度给中国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西蒙非常热爱中国,他在自传《我生活的种种模式》中称中国为我的中国,称他的中国朋友为良师益友。如今,西蒙教授虽已作古,但他永远是中国人所尊敬的长者。管理行为中的理性与决策心理学 管理理论的关注焦点,是人类社会行为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层面的分界线。管理理论尤其是关于刻意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理论,也就是关于因为最优化的不可及,退而求满意决策的理论。 管理决策的正确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它选择适当的手段来达到指定的目的就是正确的。理性管理者主要关注如何选择有效手段。要建立一种管理理论,必须进一步考察理性的概念,尤其必须要彻底澄清“选择有效手段”的含义。这个概念的澄清过程,对于理解管理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效率”和“协调”非常有益。 我们先来考察决策的客观环境,以及做出抉择的实际后果。抉择只要是理性的并且其客观条件是可认知的,它就是从多个备选方案中选出其中一个的过程。由于各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不同,所以对决策客观环境的分析,主要就是指研究抉择的各种可变的后果。 由于人们不可能永远都是理性的(功利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古典经济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当中呈现明显的“理性主义”偏向),因此在管理中就会出现决策的优劣之分,研究决策的优劣程度就有了必要。 手段和目的 “事实和价值”同“手段和目的”有关系。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具有达到预期目的的适当手段的方案才能入选成为备选方案。但是目的本身,往往只是帮助更远大目标的实现。因此,就出现了目标系列或目标层级的概念。而理性必然同构建这种手段—目的链有关。 目的层级 即使发生在生理层次上,手段—目的关系也是起到整合行为的作用。在这个层次上,肌肉张力的协调是(一种手段)为了执行简单的生理动作,如行走,伸手拿一样东西,将眼光转移到某件物体上。这些简单的动作对于成年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和自动进行的;但是儿童必须费很大力气去学习,这种学习虽然不是反射行为,但实质上完全类似于成年人在手段—目的情形下的学习。 但是迈步或抓住某个东西,这些动作本身通常又是达到下一个目的的手段。要确定哪些目的是这些动作本身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追求哪些目的是为了实现下一个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最明显的方法是:让行动主体处于在矛盾的目的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情境当中。 某些目标必须依赖于其他一些更远大的目标才能发挥作用。这个事实导致目标的层级式结构,每一层相对于其下层都是目的,相对于其上层又是手段。通过目的的层级结构,行为得以保持完整性和一致性,因为每个备选行动方案都使用综合的价值尺度即“最终”目的来权衡。但是真实行为几乎达不到高度自觉的整合。因为有意识动机的结构不是单一的分支层级式,而通常是错综复杂的网络式,更确切地说,是只有微弱和不完整关联性的要素集。随着目的层级上的等级逐渐提高(就是说有更远大的目的),这些要素的整合程度也逐渐减弱。 手段和目的的层级结构既是个人行为的特征也是组织行为的特征。实际上,目的型组织的专业化分工模式,也就是与目标实现的手段和目的体系保持一致的组织结构安排。因此,消防部门的目的是减少火灾损失,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则是防火和灭火。这两种主要手段在组织结构中一般分别由防火局和灭火队来实现。我们发现,由于后者必须散布在城市的各个分区才能达到目的,所以该单位的下一层组织单位是按照地点进行专业化分工的。 无论是对于个人行为还是对于组织行为来说,手段—目的层级结构一般都不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整合链。组织活动和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往往很模糊,要么这些最终目标没有完全形成,要么在最终目标中或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中,存在内在的冲突和矛盾。例如,公共工程管理署由于把“政府投资”和“失业直接救济”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同时当做该机构的目标,因此使得其决策复杂化了。战时生产委员会制定决策时,也必须在战争需求和平民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组织的手段—目的层级缺乏完整性,有时是因为政策制定机关拒绝确定一个政策“热”点,比方说,国会拒绝确定家庭身份和职业在延缓服兵役中的相对重要性。手段—目的联系本身有时就很模糊。比方说,“军队的目标就是打败敌人”这种说法,在实现该目的的正确战略上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争吵和冲突的余地。说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先打德国”与“先打日本”两个派系之间的辩论。 考虑这些手段—目的关系,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完全地整合自身的行为。但是,行为中的理性,恰好就体现在刚才描述过的那种不完整,有时还不一致的层级中。
【 新浪财经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