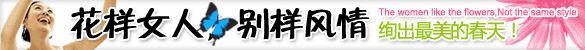|
|
赫伯特·A·西蒙:理论无边界(3)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01日 14:23 《当代经理人》
预期的难题 预期的快乐也许与现实的快乐相差甚远,这是众所周知的经验之谈。真实体验可能比预期的合意得多,也可能正好相反。 出现这种现象不仅是因为有些结果无法预期,有时就算我们相当完整地描述了抉择的结果,这种预期所带来的情感波动也几乎不如真实体验所带来的情感波动效果明显。造成这种差别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头脑一时间无法掌握所有结果,而是随着对结果偏好的转移,注意力也从某一价值要素转向了另一种价值要素。 所以,评价的准确度和一致性都受到个人能力的限制,也就是个人探索其设想结果中变动的价值要素,并在预期与实际体会中同样重视这些价值要素的能力。 这对“风险”行为来说可能是一种重要的影响力。比方说,在风险投资中,失败的结果根据以往的经验或出于其他原因让人感受越深,风险承担行为就越不可取。这与其说是失败的经历让我们赋予失败较大的发生概率,不如说避免出现失败结果的愿望变得强烈了。 用一句话来概括理性管理和非理性心理,管理理论的关注焦点,是人类社会行为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层面的分界线。管理理论尤其是关于刻意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理论,也就是关于因为最优化的不可及,而退而求满意决策的理论。 西蒙和人工智能 西蒙认为,人的思维过程和计算机运行过程存在着一致性,都是对符号的系列加工,因此,可以用计算机来模拟人脑的工作。 西蒙是人工智能和数学定理计算机证明的奠基者之一。他和纽厄尔(Allen Newell)合作的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改变了我们对人脑和电脑关系的理解。作为科学家,他涉足的领域之多,成果之丰,影响之深远,令人叹为观止。1975年,西蒙和纽厄尔两人共同获得计算机领域的最高奖图灵奖,就是对他们在这一领域成就的最好说明。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蒙的研究方向发生了重大转移,逐渐转向了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领域。西蒙认为,社会科学缺乏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性,社会科学需要借鉴自然科学严格和精确的研究方法,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同时,在西蒙看来,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所研究的课题,实际上都是“人的决策过程和问题求解过程”。要想真正理解组织内的决策过程,就必须对人及其思维过程有更深刻的了解。因此,借助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西蒙与同事纽厄尔等人一起开始尝试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行为,从而创建了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研究新领域。西蒙认为,人的思维过程和计算机运行过程存在着一致性,都是对符号的系列加工,因此,可以用计算机来模拟人脑的工作。他甚至大胆地预言,人脑能做的事,计算机同样也可以完成。“初级知觉和记忆程序(EPAM)”和“通用问题求解系统(GPS)”等人工智能软件的问世,部分证实了西蒙的预言。 西蒙在人工智能中做出的最基本贡献,是他提出了“物理符号系统假说”PSSH(Physical Symbol System Hypothesis)。在这一意义上,他是符号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基本观点是:知识的基本元素是符号,智能的基础依赖于知识,研究方法则是用计算机软件和心理学方法进行宏观上的人脑功能的模拟。符号主义的主要依据是两个基本原理:(1)物理符号系统假设原理。(2)由西蒙提出的有限合理性原理。这一学说鼓励着人们对人工智能进行全面的探索。西蒙认为,任何一个物理符号系统如果是有智能的,则肯定能执行对符号的输入、输出、存储、复制、条件转移和建立符号结构这样6种操作。反之,能执行这6种操作的任何系统,也就一定能够表现出智能。根据这个假设,我们可以推出以下结论:人是具有智能的,因此人是一个物理符号系统;计算机是一个物理符号系统,因此它必具有智能;计算机能模拟人,或者说能模拟人的大脑功能。 西蒙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另一大贡献,是发展与完善了语义网络的概念和方法,把它作为知识表示(knowledge representation)的一种通用手段,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在知识表示方法中,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是—种重要而有效的方法。这种表示法是奎林(M.R.Quillian)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来的,作为人类联想记忆的一个显示心理学模型。奎林在开发TLC系统(Teachable Language Comprehender)中用它来描述英语的词义,模拟人类的联想记忆。但用语义网络作为一般的知识表示方法,则是西蒙在1970年研究自然语言理解的过程中把它的各种概念基本明确下来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蒙和CAD专家依斯特曼(C.M.Eastman) 合作,研究住宅的自动空间综合,不仅开了“智能大厦”(intelligent building)的先河,还成为智能CAD即ICAD研究的开端。 (本文根据公开资料整理)西蒙VS法约尔 一个是科班出身的管理学理论大师,一个是实践中锻炼出来的高层经理;一个因在决策理论上的学术性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一个以创建了管理学的一般体系而成为享誉世界的前辈。可以说,西蒙和法约尔都是管理学发展历程上的标志性人物。然而,两个人却在思想方法和学术观点上有着巨大的分歧。 法约尔的管理理论主要有管理要素和管理原则两大部分,而与西蒙思想冲突的焦点基本集中在他提出的十四条管理原则上。这十四条原则主要是围绕着组织结构、效率的发挥和处理人际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西蒙对这些管理原则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评。在《管理行为》中,西蒙指出:“目前流行的管理原则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如俗话说的‘福祸不单行’一样,管理原则也总是成对出现。无论对哪个原则来说,几乎都能找到另一个看来同样可信、可接受的对立原则。虽然成对的两个原则会提出两种完全对立的组织建议。可是,管理原则里却没有指明,究竟哪个原则才适用。”他指出:这些原则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内在的逻辑往往存在着矛盾。 西蒙和法约尔的对垒,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二人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分歧。归结到哲学上,就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分歧。周晓亮在《西方近代认识论论纲: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中指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作为两种有着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想,围绕着什么是知识以及如何获得知识的问题展开,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人类知识的根本源泉是什么:是感觉经验还是先天的观念;(2)哪一种知识具有无疑的确实性和真理性:是经验的知识还是理性的知识;(3)通过哪种方法或途径能够有效地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是经验的归纳法还是理性的演绎法;(4)人的认识能力是否是至上的,它是否有一定的范围和界限。显然,西蒙和法约尔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是有差别的。但是,如果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不利于深化对他们的争论进行研究。 现实生活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往往存在着交叉认可。西蒙的理论和法约尔的原则,如果从互补的角度看,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思考。西蒙倡扬理性在管理中的作用,不过,他在经验的基础上对理性进行了限定,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缺乏经验证明的公理框架。法约尔也对自己提出的管理原则进行了说明和解释,强调原则的模糊性和灵活性,回避了逻辑上的构建。当初在还没有遇到质疑的情况下,法约尔就在《工业管理一般管理》中事先声明:“我更喜欢用原则这个词,但应使它摆脱死板的概念。在管理方面,没有什么死板和绝对的东西。”“原则是灵活的,是可以适应于一切需要的,问题在于懂得使用它。这是一门很难掌握的艺术,它要求智慧、经验、判断和注意尺度。”这一声明,几乎就是对数十年后的西蒙式批评的预先回应,令人不得不赞叹法约尔那种天才的先知。 而西蒙在抨击法约尔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吸取了经验主义的长处,避开直接的宏大叙事,以逻辑实证主义的思路构建管理学的分析方法体系。他指出:“管理文献中固然从不缺乏‘理论’,也不缺乏描述性的和经验的研究,它缺少的一直都是这两者之间的桥梁。”而西蒙本人,也宣称自己不是创立管理学理论,而是对建造这样的桥梁做出贡献。从这一点看,西蒙对法约尔的批评,恰恰又是以法约尔的研究为铺路基石的。 西蒙对法约尔的质疑,当然有充分的道理。毕竟,法约尔的管理原则缺乏相应的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所以具有自身的局限性。正是类似于西蒙的这种批评,推动着管理学理论的实质性发展。但是,西蒙的批评又不妨碍法约尔的光辉,正是有了法约尔式的前人成果,西蒙才能对人类理性的认识上取得划时代的突破。在以前撰写“与大师同行”的栏目稿件时,《当代经理人》都会通过或者面访、或者电话采访、或者Email采访,把我们采集到的中国企业遇到的问题与大师交流,聆听他们的教诲。对于西蒙,这位我们非常崇敬、但却已辞世的管理大师,我们只能通过整理他身前的精彩言论,来展示他的思想…… 问:与信息(information)相比,创业者的信念(beliefs)起什么作用? 西蒙:创业机会的来源是什么?许多人用信息的不对称去解释,但中心的问题似应是创业者的信念,而非信息。信念与经常谈论的信息话题很相关,也意味着与现实世界的相关性。但信念与信息的区分是有价值的。 但这样的信念是一些非标准的信念(non-standard beliefs),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那就是非均衡的一部分。创业的非标准信念其来源是什么?在创业者的心态中这种风险和机会(危机=危险+机会)如何取得平衡? 问:有没有人们决策不起作用的地方,对未来没有安排的可能性,那么是什么在创业过程中起作用呢? 西蒙:在奈特(Knight)著名的《风险、不确定与利润》中,做了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现实中假如存在着从不确定性回到风险的倾向,回到你可以计算概率的领域。假如你有20份创业项目可以投资,你就需要使用概率,人人都知道的大数定律,假如你能得到正确的工具,谁又关心标准差呢?有没有人们决策不起作用的地方,非但不能,甚至对未来没有安排的可能性,那么是什么在创业中起作用呢?(创业中许多情况下就是面对着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环境) 问:创业(对均衡状态)既是一个破坏过程又是一个创造过程吗? 西蒙:创业的初始条件是某种程度的非均衡吗?正是存在着非均衡,所以导致了采取行动使之回到均衡状态的动力。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否把初始条件看作是永久的非均衡状态更好呢?能不能以平和心态面对非均衡呢? 创业(对均衡状态)的破坏过程也是其创造过程吗?它是一个破坏过程,还是一个创造新的方案的过程,还是在结构上的根本变化? 问:在一个大型公司的新奇创造过程中,谁是创业者?创业过程又是怎样的? 西蒙:例如,IBM公司,是一个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也是非常盈利与成功的公司,那时成功的产品叫打卡机,然后是50年代的计算机。那是创业吗?谁是创业者,过程又是什么?是否把它看成创业,这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果说它不是创业,只是把新奇带到世界上的不同方式。那么通过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新奇产生过程,我们就会了解创业的特殊性以及创业的共同性,和一些其他的过程。我们会考虑一些更本质的问题,为了把新奇带到世界上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如杜邦发明了许多东西。历史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创业和发明的故事。他们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 问:如何定义创业效果? 西蒙:创业的效果在就业、生产率上都能体现出来,还有收入分配上,如何定义效率,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不光是产品在变,效用的功能(Utility function)也在变,还有将来出现的新效用,都会影响对创业效果的定义。 问:创业的范围是什么? 西蒙:我们讨论大学内部创业或是非赢利组织创业的时候,意味着什么?这是与个体创业同一过程,还是不同的过程,我们又能从这些过程中学到什么,谁是这些事件的风险投资商? 还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如作为市场放大效应的政府,美国历史上的修建铁路与西部大开发的例子。创业的过程是什么,谁又是创业者?也许我们可以叫那些“说客”为创业者?不知道。最近看来,在世纪之交,政府在飞机的费用上又做了许多工作。还有电子业的如ARPA规则制定等,谁又是创业者? 问:在创业中制度起什么作用? 西蒙:我想美国是在创业上最早的制度上的安排者,目前关于专利制度有许多的争论和建议,这些建议是有利于创业呢,还是不利?。这就涉及到了不同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尔·盖茨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因为他把许多创新的家伙赶了出去。另外一种看法是他只有一些小的想法,而伴随他的是自50年代开始别人的无数创新想法。因为软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他的一些想法碰巧给了他一个市场上相当重要的战略位置(先占优势?)。 再看苹果公司的例子,也是伟大的创新。站在书写计算机科学的技术历史看,苹果的创新可能是相当重要的创新之一,就象Paul所说的大创意:“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作为电脑屏幕的基础和操作系统等。也许从创业研究看,我们不应该只看个体的创业者和他们所作的贡献,还要看创新的结构和创新的法律支持体系等,是这些使得特殊的创业赢利或是大的赢利。 问:适合创业研究的方法是什么?如何获得数据? 西蒙:在创业上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如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但如何获得科学发现的数据呢?他们不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你不能坐下来对一位科学家说,请你搞一项发明吧,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或者是做两组科学家的对比实验,一组成功了,一组没有。他们非常不喜欢这样。因此在方法论上就有许多难题。当然人们也做了一些实验性的方法,如带来一组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告诉他们:告诉我砖的不同种用途。然后从他们的不同想法中辨别学生的不同独创性。最终你或许得到了砖的有趣的知识,但不是研究科学发现本身,你是研究别的。 在创业上,有无数的创业故事,但那儿都是轶闻趣事,是案例研究。我们需要得到的是一些真实的数据,而不是类似的砖的13种用法等等。我们需要方法上的创新。
【 新浪财经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