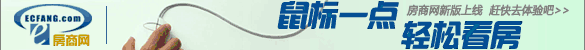|
|
秦晖:摆脱黄宗羲定律仍待努力
投资者报(记者)当年的“皇粮国税”问题
1969年我15岁时初中毕业后到广西农村插队,在百色地区田林县的壮族山寨做了9年农民。百色大概是我国唯一占全了“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边(疆)、山、穷”五项的地域,田林县则位于滇、黔、桂三省交界处,是广西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稀的一个县。9年乡村生活给我的人生道路打下的烙印是非常深的。1978年我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取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跟随我国著名农民史专家赵俪生先生学习“土地制度与农民战争史”。获硕士学位后一直在高校任教。
我的这门专业本属于历史学,而且主要是古代史。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当时在陕西师大任教的我为了研究土改前关中农村问题,每年利用到各县搞函授辅导之机,多次到各县基层档案馆查档,并接触现实农村。1994年,我从陕西师范大学调入北京后,除了任教清华大学外,还先后兼任中农信研究员、《中国农民》特约记者等职,并与农口一些研究部门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清华,从1995年起,我连续组织了几次学生对浙、湘、黔、川、陕、桂六省(区)八县(市)的19个村庄(社区)进行了考察,重点调查了224户农家,以问卷统计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对不同经济类型与发达程度的农村作了研究。就这样,我的农民学研究,从农民史延伸到现实领域。当初这样做,主要是“今为古用”,基于学术兴趣,相信马克思说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研究生涯中形成一个理念,即当代农村、当代中国是传统农村、传统中国的延伸。不了解传统农村,就不可能理解当代农村,反之亦然。
但是后来,乡村调查中看到的一些现象使我忘记了“今为古用”的初衷,不由自主地关心起农民与中国改革的未来。税费改革就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
其实,随着“大包干”以后我国家庭农业的恢复,人民公社时代国家直接从基层组织的公库里获得征、派购粮以汲取剪刀差的模式结束,农户由过去给“公家”干活而向公库领取口粮与其他劳动报酬,变为如传统时代一样自耕自食而反过来向“公家”交纳“皇粮国税”、纳赋当差。传统时代的赋役问题又以“农民负担问题”的方式再现。由此而产生的税费改革最初思路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萌芽,90年代前期,河北的魏县、南宫,安徽的太和,湖南的衡东等有些地方就自行做过“并税除费”试点,有的地方当时叫做“公粮制”等等,名目不同,意思一样。
在1995年到1997年间,我正组织学生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时,就感觉到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出现反复的苗头。比如某县教育附加费合并到正税里了,过了两年学校没钱用,财政拿不出,又出现新的教育费用。农民不满地说,要这样还不如不改,不改的话,你收了我一次教育附加,还能再收“第二教育附加”吗?现在你把教育附加合并了,好像我们没交这笔钱一样,下一任领导一看学校这么破,又向我们收钱,我们跟谁说去!
还有一种情况:这个县做试点,把什么屠宰税啦等等都平摊合并到税里了,农民说:“猪头税变成了人头税。”可是邻近县还在照样征收这个费用。于是,试点县的农民就担心地说,过了几年,他们县官一换,新来的不了解情况,以为便宜了我们,又让交屠宰税了。“这下子倒好,猪头、人头都得交税啦”。
另有些地方,90年代后期由于农民权利意识滋长,逐渐学会抵制各种乱收费,征收的“工作难度加大”了,有人便寄希望于“费改税”。调查中曾经有一个镇领导对我解释并税改革的好处时说:“并税改革的确好,过去那些统筹、摊派什么的,农民就是不交,你还真没办法。如今一合并成皇粮国税,农民再不交,就是抗税了,我就好派出警察抓人了。”如果并税改革被理解为政府以前收费比较难,现在改成收税,就可以用强制手段,税费改革就容易出麻烦了。
当时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并且联想到历史上也有过许多类似现象,于是我根据调查报告写了一些文章。
“定律”提出的前前后后
1994年第二期的《改革》杂志刊登了我写的《农民负担问题的发展趋势:清华大学学生农村调查报告之研究(四)》,其中我第一次提到“黄宗羲定律”。我当时认为,税费改革势在必行,而且这种改革在技术角度上讲的确是合理的。“明税轻,暗税重,集资摊派无底洞”,搞历史的知道,中国从来就是这样,这叫“正供有限,而横征无穷”。所以要解决农民负担,就得从解决收费开始,正税相对来说本来就不多,农民如果只是交税的话,可以说是相当“幸福”的。但是,在传统政治条件下搞税费改革,最麻烦的就是怕跌入怪圈——农民负担简而复繁,出现反弹,反而越改越重。古代很多人,包括清代的范清丞、明代的黄宗羲、宋代的李心传、唐代的陆贽等等很多人表达过这种担忧,反对归并税则。现代一些史学家也注意到这种现象,例如上海师范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家范、谢天佑两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辑刊》上发表的《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一文中提到了黄宗羲对“积累莫返之害”的批判。但是那个时候“大包干”的农村改革尚未铺开,农民作为“皇粮国税”交纳者的问题也未凸显,黄宗羲的这些话作为纯粹的历史问题也只有极少数史学家注意。
这一方面也是由于过去我们的历史书一般都肯定这种改革,而把反对这类改革的声音一概视为“保守派”,不予好评。其实这种改革的反对者历来有两种:一种是旧税制下有既得利益者的代表,例如旧税制种类繁多,千头万绪,农民不懂上司难查,胥吏便得以上下其手,搭车寻租,中饱私囊。他们当然不喜欢简化税则。还有的旧税制有许多优免规定,有权有势者可以借此规避负担,转嫁于无权无势者。新税制取消了优免,也会招致这些人的反对。但是,还有一种反对者,如前述的黄宗羲、陆贽等人,他们并不是基于既得利益者的立场,而是的确看到了当时税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且往往是透过当时税改的一些短期效益,在主流意见一片乐观的气氛下发表冷静的看法,其实相当难能可贵。当然由于那时的历史局限,他们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有时还得出了反对改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结论,提出问题的深刻与给出答案的浅薄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今天应当能够超越这些局限。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博大精深,历史学因此历来是显学。但是历史内容如此丰富史料如此浩繁也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囿于精力与眼界所限,许多专家只能关注中国历史的某一时段,形成传统中国史学中“断代史”研究特别发达的特点。而缺少长时段的通史眼光容易导致所谓“断代本位主义”,人们往往根据当朝的记载高度评价某次改革一举解决了什么什么问题,而其实这种问题在以前的朝代中就曾经被“解决”过,在以后的朝代中它又重复出现并再次被“解决”。例如取消力役,汉之更赋,唐之丁庸,宋之免役钱,明之银差、条编,都曾被说成是以赋代役而在历史上解决了力役问题。然而实际上以赋代役后、赋外又生新役的循环一直在重复,直到清末还有“地丁属地,差徭属人”,民国时代还有拉夫派差的,今天的农民不是还正式规定要出“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吗?这次税费改革又把这“两工”合并取消了,但愿未来不会再次向农民派差。力役取消而又复起,但历代所征收的代役钱,却从没有退还过。农民负担怎么会不重呢?还有由按户口征收转变为按地亩征收,亦即人头税并入土地税,也是重复了许多次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把现实调查材料与历史资料结合起来谈论“黄宗羲定律”。然而在1997年当时,税费改革仍然还在小范围试点,并没有在许多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实行,所以,这篇文章影响不大,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