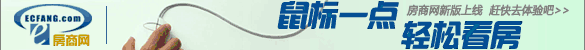|
|
黄宗羲定律为什么是封建王朝一个怪圈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大儒,在明王朝灭亡后,痛定思痛,以“天下为公”的儒家信条为武器,不仅对明王朝,而且对整个传统体制都进行了系统反思。其中,他批判了“一条鞭法”,而要求恢复赋税分征。实际上,他的评论远远超出税制本身,涉及到的是传统帝国千年来农民负担问题以及解决方法的根本缺陷。
包括一条鞭法在内的历代“并税改革”,连同“易知由单”这样的配套措施,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屡屡出现。由于在专制王朝统治费用刚性增长的条件下,财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不能“量入为出”。为克服横征乱派之害,减少税收中的流失和官吏层层中饱私囊,并税除费,简化税则,就成了主流改革思路。仅在明清两代,便搞过“征一法”、“一串铃”、“地丁合一”等等。目的就是把从朝廷到基层的明暗正杂诸税“悉并为一条”,“一切总征之”。同时下令,不得再征他费,还发给农民法定税目表“易知由单”,允许农民照单纳税。
但是,传统社会,农民没有任何民主权利,上面到底征多少税,农民是不能控制的。这样,合并税费有个很大问题,它原来有各种各样的名目,有了这些名目,新的巧立名目,往往空间比较小。比如说,官府常向农民派工,即所谓劳役。劳役经常干扰农时,农民很受劳役之苦,陈胜、吴广以及隋末农民起义都是因为劳役太多而起。官府为此进行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劳役并到正税里,在正税里,多征一大笔钱,一般在财政上叫“代役税”或“免役税”。理论上说,国家有了这笔费用,就可以雇人干活,农民就不用出劳役了。实际上,传统中国官僚太多,开支大,经常出现财政危机,一旦有了财政危机,拿不出这笔钱来雇人,农民又要出劳役。官府已经征收了农民免役税,你又没把这笔费用还给农民,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而且,并税后,各种名目没有了,恰好为后来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用不了多长时间,人们就“忘了”正税已经包括了从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黄宗羲精辟地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就这样,历史上每搞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这也是专制王朝时代的一个怪圈。实际上,在传统中国,主要矛盾不是农民没有土地,而是有土地也种不了,因为各种各样的赋税迫使农民不得不弃田流亡。但是,自古以来,“正供钱粮”通常不是太高的,但农民的付出却很多,主要就是各种各样的杂派。因此,农民负担问题,历史上一直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
从“并”到“免”:
农村税费改革的突破
到了2000年,税费改革全面推广时,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许多报刊、国内主要网站纷纷转载。不久,又应有关方面的建议,撰写《税费改革、村民自治与强干弱枝》的长文,就税费改革中的问题提出建议。
文章发表后,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当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在2000年年底,也就是中央在安徽召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总结会议前夕,在《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一文上做了批示,全文如下:
“请怀诚、耀邦(刘坚)、马凯同志阅。要跳出‘黄宗羲定律’,农村税费改革就必须坚持‘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控制税赋的绝对额,长期稳定不变;就必须在财政上厉行‘量入为出’而杜绝‘量出制入’。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温家宝
十二月廿八日
以后,温家宝以及农口的许多人,在许多场合都提到这个定律,指出要跳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这一批示中基本上把我文章中的几点建议都点出来。比如一定要稳定税费的绝对额,不要搞什么收入的百分之几这类的软性相对指标。另外,财政方针一定要量入为出,绝不能量出制入。
历史上传统财政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量入为出,可以从农民那里拿多少,就办多少事。不铺大摊子。但封建时代,往往采取量出制入,而不是采取量入为出。官府需要什么就向农民征多少。所欲所求无止境,征收也就控制不住了。所以温家宝提出稳定税额,绝对量不变,财政上要量入为出。
在那次农村会议上,温家宝提出乡镇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实际上,传统中国出现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体制造成的。农民没有真正的公民权,没有“无代表不纳税”的机制。所以,解决的根本途径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在目前的方案中,首先是社区开支与社区民主、村民自治挂钩,“一事一议”,就是凡是在农村社区使用的这些费用,一定要由农民讨论。以前我们常说,赋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农民并没有觉得是用在他们身上了。应该把权利交给他们,变成“民之所用,民之所议,民之所定,民之所出”。当然,这只是社区的开支,社区以上,乡镇财政,县财政,用“直接民主”的办法搞“一事一议”是很难做到的。那就需要发展代议制。乡镇政治体制改革后,就不要设那么多人,那么庞大的机构了。
再就是国家应当下决心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不要把它推给基层财政,实际上还是推给农民。在如今许多地方县乡村财政都很糟糕的情况下,中央财政、至少是省财政应当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
当然,更进一步的做法是彻底正名。既然“并税除费”难保不重蹈历史覆辙,讨论中不少人就提出干脆取消农业税。反正它占国家收入的比重不大,收税成本又很高。但我当时认为,也不必特别规定农民不缴税,这会导致一种误解,仿佛农民占了市民的便宜、得了国家多少恩惠似的。过去历史上一些开明皇帝或者未必开明但喜欢作秀的皇帝也曾经搞过减免赋役乃至全面蠲(juan)除,但农民获益或者不能持久,或者只是口惠而已。这当然首先是由于农业社会不取之于农则国将不国,不像工业社会可以靠非农税收,但是当时农民作为臣民处于被动地位也是一个原因,统治者一时向善则蠲(juan)免之,一时纵欲而苛征之,农民只能祸福由之了。
而当代欧美农民实际上处在国家高度保护之下,国家给他们的补贴远远多于他们交的税。但他们一面享受补贴,一面还是要交税的。交税不仅是公民义务,同时也包含“纳税人权利”嘛。问题是税制要公平,不能有身份性歧视。其实只要城乡一视同仁,按所得税起征点以上,该交多少就是多少。起征点以下不分城乡都免交,城乡平等的“低保线”也许条件还不成熟,城乡平等的“起征线”应当是完全可行的。当时公布的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折合月计还不到起征点。所以只要统一了“国民待遇”,大多数农民是不该交所得税的。
那么什么叫“农业税”呢?它似乎既不是所得税(没有起征线),也不是营业税或增值税(不区分自耕自食部分),更不是地租(我们现在并不讲土地国有制,也没有契约化的租佃关系),好像也不能说是资产税(法律并不承认土地是农民的私产)。其实它就是过去所谓的皇粮国税,是与农民的“身份”相联系的义务。如今是公民时代不是臣民时代,不要再专门向农民征收那种“身份性贡赋”了。历史上,还有15岁以下60岁以上“不课”之说,现在一些农村税征到100岁。某地曾经“正面报导”过一个102岁农妇徐老太在“负担减轻”后“高兴地将今年(2002年)176元的农业税费交到村支书手中”。而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报导说这位百岁老人交纳的税费并不是村干部乱收费,而是“合同卡上规定的”。这意味着“法律”要求她继续承担缴税义务。 这种义务是“公民义务”吗?恐怕传统时代正常的臣民义务也不至于此吧。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