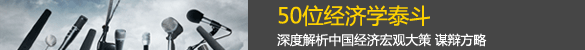我国黄金生产60年全记录
作者:刘山恩
2007年,全球黄金行业发生了一个大新闻:中国取代曾连续百年雄居全球产金第一位的南非,成为新的黄金生产领军者。但这一新闻并未在国内引起很大波澜。这是因为在业界看来,中国产金量超越南非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2006年,我国黄金产量居南非、美国之后列全球第三位,对于2008年的产金预期目标是“坐三望二”,即可以稳定在第三位,也有可能超过美国而跃居第二位,但即使有两位数的增长,也难以超过南非。
2008年初,在我国公布2007年产量之前,已有国际组织宣布,我国以274吨的产金量超过了南非的272吨,成为新的世界冠军,但我国公布的2007年产量为270.491吨,仍低于南非的272吨。因此,有关国际组织发布的消息并未得到我国的认可。
我国公布产金量后,黄金矿业服务公司(GFMS)正式发布了2007年全球各国产金量排序,把南非产金量向下修订为269.5吨,而将我国产金量向上修订为280.5吨。因而即使依照我国的统计口径,也超过了南非成为全球第一——虽然仅仅是0.36%的超越。
0.36%是一个微小的超越,但对于全球黄金行业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新纪元的开始;而对于我国来说,这是对国内黄金工业由小到大的发展历史的最好诠释。
1949年,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从新中国诞生之日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把振兴经济、发展生产作为第一要务,但对人类绝对财富——黄金的生产,国家却采取了一种抑制其发展的政策。这是当时的特定政治与经济环境所决定的。
新中国的领导者稳定人民生活、发展经济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通过货币贬值,在一年多里就把民众多年积累的财富剥夺得一干二净。1947年7月,物价比内战前上涨了6000倍;1948年8月,蒋介石又以总统紧急令的方式颁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宣布废止法币,按1∶3000000比例兑金圆券。
该办法虽然规定金圆券含金量为0.22207吨,但仍是不能兑换金银的纸币,原定发行20亿元,但实际却发行了130多亿元。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量比1937年6月增加了1445亿倍。以购买力计算,1937年可以买两头牛的100元法币,到1949年5月仅能买一粒大米的2.54‰。
如果不把严重的通胀抑制住,人民生活安定根本无从谈起,新政权更难以巩固。因此,抑制通胀、稳定物价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战线上打响的“准战役”。抑制通胀的关键是发行新货币,但由于民众饱受通胀之苦,普遍信任金银而不信任纸币,所以人民币的发行流通曾遭遇信任危机,刚刚流通出去很快又返回来——民众不敢存人民币,甚至有些商店还拒收人民币。投机分子利用民众的恐慌心理,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金银炒卖风潮。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让金银退出货币流通,才能保障人民币迅速占领市场。于是,对黄金进行管制,禁止黄金自由流通买卖,便成为当时必须采取的政策。
黄金作为人民币当时的对立物,成为稳定经济的异类力量而受到管制。另外,当时我国的外贸主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易货贸易为主,所以当时黄金硬通货的功能也隐形化了。于是,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黄金成为被人们遗忘的“丑小鸭”,未能得到国家的关注和重视。
1950年至1957年,国家对黄金工业的投资每年平均仅100多万元。在这8年里,全国黄金工业增加了400吨/日的处理能力,却自然消失了300吨/日的处理能力——也就是说,实际上只增加了100吨/日的处理能力。这期间,黄金工业几乎是以吃历史老本的方式生存着。1949年,我国黄金产量仅为4.073吨;到1962年,全国黄金生产跌至最低谷——年产仅为3.653吨,下降10.31%。
从1949年至1962年的全国黄金产量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段时期我国黄金生产处于徘徊状态,不仅产量低,而且发展很不稳定,进一步退两步,多数年份的环比是负增长的。
黄金成为被遗忘的“丑小鸭”,在新中国历史上的时间并不长。到1957年,政策就发生了根本性调整。这一年,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大力组织群众黄金生产的指示》,要求“各省、自治区必须把黄金生产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事业来领导,按期完成黄金生产任务。”当时政策调整的动力主要是国家用于外贸支付的需求上升。
“一五”期间,我国从苏联购买了164项工业项目的装备;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向我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留下了部分装备。这些装备形成了我国对苏联的65亿元人民币欠款,按汇率折算约合20多亿美元。
偿还这笔欠款需要大量外汇,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少得可怜,平均只有3亿多美元。另一个办法是使用外贸顺差,用外汇结余还债,但在1950年至1957年的8年中,我国外贸有6年是逆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借外债来还债,于是我国又从苏联贷款。当时我国工业落后,出口工业品的能力很弱,只能以农副产品出口予以偿还。但是,很快农副产品的国内供给与需求出现了越来越大的矛盾,导致农副产品出口减少,出口合约难以履行。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决策者把解决问题之道放在了增加黄金生产上,因为当时增加黄金生产就可以增加外汇供给。这就是国家调整政策要求黄金增产的根本原因。然而,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黄金这只“丑小鸭”立即就可以变成一只“白天鹅”,黄金工业从此走上了一条艰难跋涉之路。
临危受命的我国黄金工业,的确过于寒酸了一些,除了清朝末期留下的一点家当和日本侵略者为掠夺资源在东北地区实施的开发项目有些遗存外,再也没有什么本钱了。所以,我国迈开发展黄金工业第一步时,只能依靠群众运动。
1957年,国务院曾下发了一份要求大力组织群众黄金生产的指示。从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要求看,通过以群众运动来组织工业生产,是一种粗放、低效、低水平的生产组织方式。但这也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一是当时中国深受群众战争观念的影响;二是当时没有靶区可选,又无储备资源可用,只能通过发动群众广泛寻找,以解燃眉之急。
这种以群众运动发展黄金生产的选择,其实际效果自然寥寥。虽然国务院反复强调,并采取多种经济刺激方法,但黄金产量依然低迷,1962年产量甚至跌至历史低谷。直到1975年,这一历史阶段才因黄金工业再出发而结束。
黄金生产从群众运动开始转向大工业生产方式,一个突出的标志是1965年中国黄金矿产公司的成立。该公司成立后,使各地黄金生产形成了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的工作体系,并陆续组建了地质勘查、基建、生产、科研、设计、教育等专业队伍。公司先后接管和建设了39个直属企业和事业单位,初步形成了当时被称之为“托拉斯”的黄金生产联合企业,使我国黄金生产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大工业生产体系。
从1949年到1962年,14年间我国总计生产了73.105吨黄金,年平均产量为5.23吨;而从1963年至1975年的13年间,我国总计生产了128.72吨,比前13年增产55.545吨,增长率为75.9%,年均产量为9.9吨。这表明黄金生产方式的调整是十分必要的,但“文革”的冲击对大工业生产效率的发挥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导致我国黄金生产未能走上快速增长之路。
1975年是我国黄金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王震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开始亲自抓黄金生产,这表明最高决策层对黄金行业的更大希望和对现状的不满。自1975年以后,我国黄金工业再出发,进入了一个持续增长的新时期,并历时达20年之久。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总计生产黄金约4081.246吨(2009年产量以10%增长率计算),而1995年至2009年黄金政策转轨期和转轨后的14年,我国所生产的黄金占总产量的71.22%,为2905.701吨。这14年的产金量是前46年产金量的2.48倍。
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我国黄金工业完成了一个靓丽的转身,开始逐步找到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黄金工业发展之路。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