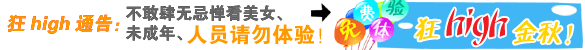|
《歪嘴男人》中,福尔摩斯轻松破案,布雷兹特里特巡官问:“我想知道您是怎样得出这个答案来的呢?”福尔摩斯回道,“全靠坐在五个枕头上,抽完一盎司板烟丝得来的。”
拥被高卧
勤心苦胝、早睡早起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美德。而年轻时代的华尔特·惠特曼,向来是
反面教材:他大约上午11:30到报馆工作,12:30准时离开,午休2小时。餐后,工作1小时,然后便进城闲逛。但汤姆·霍金森出版《如何懒散》一书,对此不以为然。他说,极权者所以反对闲人,是因为后者既不生产没有用的东西,也不消费没有用的东西。更可恶的是,他们还不被监视,不在控制之中。霍金森因此怀疑,我们反对懒散,根本不是出自人性,而是被几千年来的宣传攻势洗脑。譬如,《圣经》中就经常有这样的主题: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能: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人是被造出来做工,而不是思考、感觉或梦想的。”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这样写道。他还补充:“每一个偷懒的时刻都是在叛国。”———一下子把这个观念提到国运的高度。凌晨4点笃定起床的约翰·卫斯理,则写过一个题为《早起的义务和益处》的布道,称赖床有害健康,并用科学术语进行论证:“人体长时间沉浸在温暖的被褥间,达到过热状态,将导致肌肉柔弱和松弛。同时,神经趋于衰弱。”因此,《英文字典》编纂者、18世纪英国文坛巨匠约翰逊博士尽管以著作等身傲视群雄(他旅居牛津期间,自认才智过人,曾着一袭长袍“招摇过市”,也不得不因为自己的慵懒而自责。29岁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主啊,给我力量……让我补偿我在怠惰中荒废的时光吧。”20年后,因情况仍未改善(他的传记作者詹姆士·包斯威尔证实,中午12点去他家时他多半还在“拥被高卧”,除非有“博览群书的仕女”来访,“惟一能使他从热被窝中,提早2小时起来的”是波顿的《忧郁解析》一书),于是他决心要“早起,尽量不能晚于6点”。翌年,6点起床的誓言迟迟未能实现,他又下了决心:“我打算要在8点钟起床,尽管这算不上是早起,但已经比我现在起床的时间早多了,因为我经常要拖到下午2点钟才起来。”但霍金森说,没有赖床———睡眠学者称之为“迷糊”———就没有思想,中午12点才起来的笛卡尔等就是证据。他还用福尔摩斯做例子:遇上棘手的案子,福尔摩斯常衔着烟斗在床上呆上好几个钟头。《歪嘴男人》中,福尔摩斯轻松破案,布雷兹特里特巡官问:“我想知道您是怎样得出这个答案来的呢?”福尔摩斯回道,“全靠坐在五个枕头上,抽完一盎司板烟丝得来的。”
疾病与快乐
懒惰和工业的战争并非始于今日。17世纪,每周劳动时间极不规律,周一神圣不可侵犯———它是非法定的休假日,俗称圣礼拜一。1681年有观察家写道:“织布工们,礼拜一普遍地喝得七倒八歪,礼拜二是头疼的时候,礼拜三则用来四处找工具。至于补鞋工,他们礼拜一宁可被绞死,也不理会鞋神。”我们为什么生病?医学诊断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事实上,患病是一种找回失去的懒散时光的方式。这一点,所有的孩子都有体会:整天在床上,没有作业,被悉心照顾,突然间所有人变得很友善。对成人而言,生病———当然是没有性命之忧时———也会被欢迎。可以像福尔摩斯那样穿着睡袍,在房间里游荡。尽管肉体不适,但却思维激荡。尼采说,“毁灭我的,同时令我强壮。”当然,特殊时期除外。据弗里德里克·F·卡特赖特和迈克尔·比迪斯《病症与历史》一书记载,“1348年,鞭笞派将信徒编成组,每组有一个领导人,穿一种特殊服装,要按规训生活,并按一定的仪式进行公开的和私下的自我鞭笞。”因为他们认为黑死病是神施加的一种惩罚,所以试图用鞭笞处罚自己来转移神的处罚。康复,是一个被忘记的词。在止痛药和镇定剂发明之前,疾病不会被掩蔽和忽视,它们被尊重、倾听,需要时间来解决。当年,塞缪尔·佩皮斯为了排除肾结石,经历了相当痛苦的手术,他不可能在36小时后便匆匆赶回办公室。他有理由在40天的康复期中游手好闲。苏格兰作家史蒂文森1873年病倒时,时年23,诊断结论为“神经衰弱,并有肺结核症状”。医生开出的处方则是:在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与地中海之间的假日旅游胜地里维埃拉度过一个冬季。这一点可使他“完全免于忧虑和恐惧”。
闺房苦旅
这些年,旅游业越兴旺,反旅游派的声音越刺耳,与霍金森“居家是最好的懒散”的思想遥相响应。反旅游派的鼻祖是19世纪的法国唯美主义者、在内务部做了30年公务员的于斯曼,18世纪的德国大哲学家康德,18世纪另一个法国人德麦斯特。于斯曼写了本小说叫《反自然》,主人公德泽善公爵是个隐居巴黎郊区的颓废主义者。德泽善的故事比较有意思。有一天,他在读狄更斯的书时突然产生了去伦敦一游的欲望。德泽善接着来到城里,订了张巴黎到伦敦的车票,置办了雨伞和圆顶硬礼帽之类的标准伦敦行头,行前还逛了英文书店,然后在一家英餐馆吃饭。在那儿,他吃英国牛排,看“牙齿大得像调色刀”的英国女人从门口进进出出,一直呆到他那班火车出发,才发现不必亲身前往,伦敦就这么回事了。“就这样,他埋单离开餐馆,乘头班车跟他的大包小包、旅行手袋、雨伞和手杖一起回到他的山庄,从此再也没有出行。”康德的旅行经历更可怜,他的一生差不多都在普鲁士东部的两个小镇度过,一个叫哥尼斯堡,一个叫加里尼格勒,两者方圆都只有几英里。康德从未见过哪怕一座山,他仅有的旅行是每天下午按时在小镇荡一次马路(据说,时间准确到镇民可按他路过其门口的习惯时刻来校准闹钟),估计也就一二英里。顺便一提,康德终身未娶,他跟一个“有教养的俏寡妇”见过一面,只是还来不及算好婚姻的收支问题,人家就结婚了。另一位姑娘亦曾令他想入非非,但在决定求婚前传来了她已出洋的消息。这一切没有妨碍他严肃讨论包二奶是否有令“人类等同于禽兽的危险”的问题。旅程比康德还短的是德麦斯特。1790年,他开始了一次环卧室旅行,并据此写了本题为《闺房苦旅》的游记,他做得最多的是在仰望星空时提升道德。从这本书看,德麦斯特到过的最远地方是窗台。不但如此,霍金森还指责我们的时尚把性事都弄成一门难度系数高企的技术。这就像珍娜·詹姆斯最近的畅销书《如何把爱做得跟A片明星一样》中谈她拍最劲爆的镜头时,演对手戏的男星花样百出,以致“要跟他眉来眼去就像在过山车上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傅浩(Robby/编制)(来源:金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