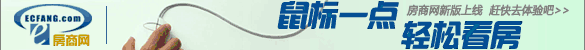|
|
宋大公子(中)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在被迫加入蒋介石政权之后,宋子文的最大贡献是,以巧妙的手段对全国的企业家集团进行了利益上的绑架。
自北伐军进入上海的第一天起,它就把发行公债当成募资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在一开始,由于缺乏确实的信用保证,公债的发行十分困难,银行家们常常以此来要挟政府,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了摊派和绑架勒索的恐怖手段。金融投资出身的宋子文对银行家们的心思当然了如指掌,从1928年春季开始,他重新设计了公债发行的游戏规则。
具体的办法是这样的:当政府宣布发行一笔公债的时候,先将这些公债存入认购的银行,以此从银行取得现金贷款,一般来说,政府取走的现金相当于存入债券票面价值的一半。根据上海钱业公会留存的资料看,从1928年3月到1931年11月,该公会总共购入债券3060万元,而实际贷给政府的款项是1562.5万元。等到公债公开发行后,银行可以将债券直接投放到上海的证券交易所进行投机交易。这种优惠的贴现政策一下子让购买公债成了一个十分诱人的生意,公债的平均年利息是8.6%,加上大量的贴现,公债的年收益率达到了20%以上,有的可高达40%。当时,银行给工厂的年贷款利息一般是6%-8%,贷给商业企业的年利息是10%,与购买公债的暴利空间无法相比。另外,将债券在证券市场上进行炒作交易,还可得更大的收益。
这简直是一个无法抵挡的诱惑。全中国的银行家们当即进入了宋子文设计好的游戏圈里,特别是资本最为雄厚的上海银行家们纷纷购买公债。此后的十年中,中央政府共发行了24.12亿元的公债,其中七成卖给了这些自诩为全中国最聪明的人。
“公债热”导致了三个结果:第一是公债发行从“天下第一难”顿时变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政府凭空拿到大笔资金,用于军事活动和工商业投资。第二是形成了一个狂热而危险的投机市场,上海金融业超级繁荣,私人储蓄和民间游资被导入政府行政性活动中。在1930年代的中前期,上海市民人人炒作国库券,用美国学者亚瑟·杨格的话说,“投机成了上海人的一种生活的道路。”第三是银行家们从此被政府“绑架”。由于新公债可以用一部分抵充旧公债,各银行为了维持旧债,便不断地购买新债,掉进了一个“循环式的陷阱”,而政府只顾借钱应付眼前,根本不考虑偿还。陈光甫、张公权等人在一开始也曾颇为担忧这样的做法将动摇银行信用,但是,在宋子文的强势推导和当前利润的诱惑下,终于不能自拔。据民国学者章乃器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文中的计算,到1932年前后,银行所持有的全部证券中的80%都是政府公债。因为有那么多钱借给了政府,他们不得不乖顺地坐到同一条船上,平等关系从此终结。台湾的中国经济史专家王业键因而评论说,“上海银行家的这种合作不仅解决了政府的经济困难,而且加强了政府对商业界的控制力量。当各个银行的保险柜里塞满了政府的债券时,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积极参与了这个政权的表现。”陈光甫、张公权、宋汉章等人一向重视自己的独立性,可是后来相继进入政府服务,大半缘于此。
可是,如果政府真的兑现20%到40%的利率,那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意。在后来的十来年里,因政局动荡等原因,政府强行规定偿还的公债打折扣,有的甚至借故不还——那时候要惩戒一个企业家实在太容易,只要从抽屉里拿一顶“奸商”或“通共”的帽子就可以了。在政局动荡之际,公债的现货和期货市场价格每每上演大跌景象,民营银行损失惨重,从此再不能与国家力量抗衡。在这场政府与民间的“猫鼠游戏”中,以后者的鼻青脸肿、投告无门而告终。
在通过改变公债发行规则诱惑银行家之外,宋子文还同时设法控制了上海的证券交易市场,而整顿的对象就是蒋介石当年曾做过 “红马甲”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了。该所自1920年创办以来,每一届军阀政权都视之为肥肉,要么扬言取缔,要么层层加税。现在终于逃不出蒋政权的手心了。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规定每一地区只准有一个有价证券的交易所,其他的交易所一律合并在内,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中交易量最大的棉纱交易率先被并入国营的纱布交易所。接着,各类交易物品被相继归并,证券部分并入证券交易所,黄金及物品交易并入金业交易所,到1933年秋,已成空壳的证券物品交易所被整体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
1931年9月18日,日军攻击满洲,爆发“九一八事变”,中日变成仇国。宋子文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很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对日本的软弱态度,日军入侵热河后,他带着支票飞到北方说服张学良坚决抵抗,并声称:“日军如来侵,我决以全国力量应付。”
为了遏制日本势力,他在1933年5月提出了两个针对性的经济政策,一是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纸品提高8%到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这当然大大有利于国内的民族企业。二是倡议组建一个由英、美、法等国参与的国际协商委员会,对这些国家的在华投资提供更为优惠的政策,他的计谋是,刺激英美企业对中国的投资,从而增加日本侵华的国际阻力。宋子文的这两项建议受到国内企业界的广泛欢迎,尽管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银行家们一再地上宋子文的当,吃足了他出尔反尔的苦头,可是在整个国民政府的决策层里,他还是惟一的“朋友”。到10月份,他们再次放弃不买公债的决定,认购了6000万元的关税库券,并再借给政府1500万元。
可是,宋子文的反日、亲英美策略与蒋介石的既定想法显然格格不入,日本人更是对宋子文恨得牙痒痒。据《申报》的报道,1933年8月,宋子文访美返国,海轮在横滨中转,日本政府公开声称他是不受欢迎的人,不让他上岸。他们还想尽办法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一定要把宋子文赶下台。10月25日,宋子文被迫宣布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职务,公开理由是“健康不佳”。据胡汉民日后回忆,宋在私下对他说,“当财政部长和做蒋介石的狗差不多,从今以后,我要做人不再做狗了。”宋辞职后,上海的公债市场再次爆发恐慌,用《时事新报》在当时的报道描述是“垂直暴跌”。
宋子文辞官后,休养了几年,到1935年4月,重新回归蒋集团,执掌国营化后的中国银行。这时候的他,呈现为一个典型的官商角色。
当时,受全球经济危机的波及,中国的民族产业面临崩溃的困境,特别是第一大产业纺织业,更是危在旦夕。惟一可能援救者,就是财力雄厚的国有银行。当时的 “纺织大王”申新公司的荣宗敬——也就是荣毅仁的大伯——就有过一次与宋子文交手的经历。
宋荣关系一向不错,荣宗敬多次登门求援,甚至写下口吻极其卑微的信函曰,“宗敬有心无力,不能有所主张,请于公暇赐一电话,约定地点与时间,俾得趋前领教,以便遵行。”宋子文诺诺多时,一直不置可否。有一次两人面谈,荣宗敬一如既往地大倒苦水,宋子文倾耳听着,突然,他用十分轻描淡写的口气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荣宗敬当场目瞪口呆。
下转46版
上接44版
数日后,宋子文终于拿出拯救计划:中国银行将申新所有9家纱厂全部收下,然后发行企业债券,以新债券还旧债务,所有债务分为营运贷款、不动产抵押借款、银行钱庄无抵押借款、个人储蓄存款和荣家存款五等,依次进行偿还,并内定中国银行总稽核霍宝树为申新总经理。宋子文给出的惟一诱惑是,申新所欠银行和钱庄的借款利息均由一分减为五厘。此案等于把荣家从申新一脚踢出。
这是申新搁浅以来最大的危机,也是荣氏创业30多年来最凶险的时刻之一。宋子文的政商势力远非陈公博之辈可比,他蓄谋半年,赫一出手,荣家幸存的机会已经渺茫。当时担任荣宗敬助手的是荣德生的大儿子荣伟仁,他在一封信中披露了家族担忧:“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事关股东血本,生死问题,非努力理争不可。”
荣宗敬四处找人说情,竟没有人敢于出面得罪宋子文。1936年2月12日,宋子文在自己的家里召集申新的三家大债权人开会,决定申新的命运。与会5人,分别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徐新六、上海银行的陈光甫、中国银行的宋子文、汪楞伯和霍宝树。这时,荣家兄弟已如盘中之物,颓颓然而任人分食。
会议开时,陈光甫居然称病没有到,替他来的是往来部经理李芸侯。宋在桌上特地摆了个大蛋糕,是为庆祝时用的。
会议是下午2点开始的,宋子文叫霍宝树把打印好的整理申新的英文文件逐段念,念一段,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最后,李芸侯发言,他讲话有点结巴,但是意见却表达得很清楚:“这个办法,敝行不能同意。”宋惊问:“光甫已同意了!”李说:“这笔款子是我放的,所以归我负责。照这办法,我行肯定要亏本,还望宋董事长大力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李所谓的亏本,是指申新欠上海银行1200多万元,年息由1分降到5厘,每年要亏至少50万元。宋说:“那么如何办呢?中国银行也是同意的。”李说:“或者把上海银行借给申新的款项转给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发行银行,问题不大,我们行就承担不了。”众人听了,脸色骤变,宋说:“这样就不能再谈下去了。”会议不欢而散,桌上的蛋糕没有人碰过。
荣家显然是幸运的。在那次经济危机中,国营事业集团通过接收、控股等手段进入到原本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大量轻工业领域,如烟草、面粉、粮食加工等等。仅中国银行一家就控制了15家纱厂,约占华商纱厂锭子总数的13%。
1935年的某日,“火柴大王”刘鸿生因从事多元化经营而导致资金困难,他向多年交好的宋子文求救:“最近银根越来越紧。我有几笔到期的押款,银行追得很急,希望中国银行接受抵押,帮我渡过难关,您看可以吗?”宋子文冷冷地问:“你用什么作抵押呢?”刘答:“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宋以嘲笑的口吻说:“O.S.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O.S.是刘鸿生的英文名字,他日后回忆说,这是他终生最难忘的一刻。
来源:经济观察网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